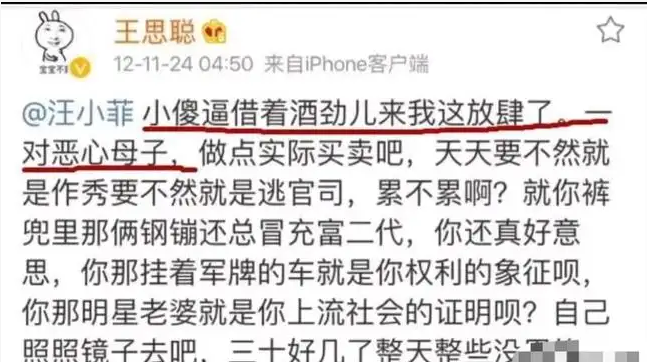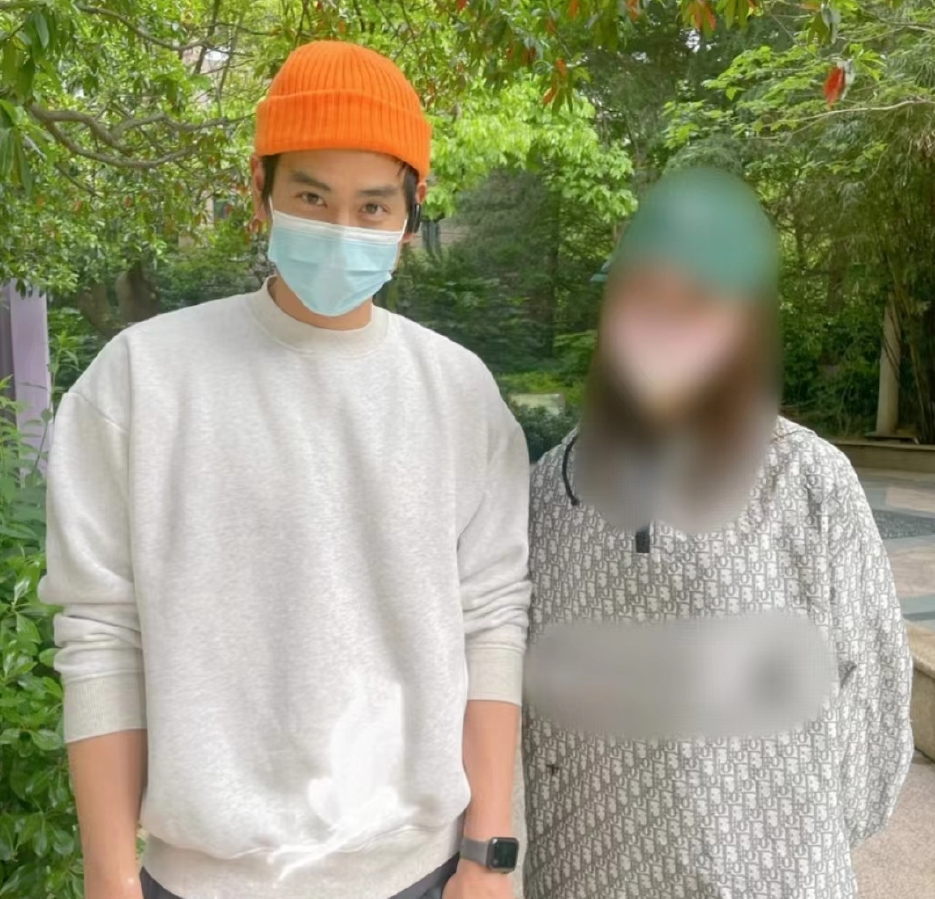这是一本大书。说它是“大书”,不仅在于它的厚度,还在于它所带给我的那些深刻、宏大、真实而无限的东西。
“如果生活中没有某些无限的、某些深刻的、某些真实的东西的话,我就不会留恋生活。”
对于凡高来说,在他短促的37年的人生岁月中,他已经感受到了“某些无限的、某些深刻的、某些真实的东西”,他把这些感受源源不断地倾吐在画布上,笔触急迫而平静,浓烈的色彩在笔下奔流,于是,我们看到了广阔的麦田,或怒放或含苞的向日葵,开花的杏树,精神病院的医生,邮递员的妻子……当他意识到自己再也无法感受这些“庄严的悲哀”,他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
此书是凡高的书信体自传,由凡高写给弟弟提奥的几百封书信连缀组成。这样的文体使我在阅读这本书的日子里,经常会产生一种狂妄的幻想,试图走近这个伟大的灵魂,理解他的艺术,理解他的生活,理解他孤绝的求索。我看到了这个灵魂深处跳动的火焰,它熊熊燃烧着,始终不曾熄灭,直至把自己燃成灰烬。正如凡高所说,即使“在上流社会中,以及在最好的条件与环境下,一个人也一定要保持隐士的某种原始的性格,否则他就失去了自己的根子;一个人决不可以让自己心灵里的火熄灭,而要让它不断地燃烧。”
从早期对上帝的迷恋,到走上艺术的道路,凡高逐渐学会了倾听自己内心深处的声音:
“啊!我愈来愈感到人民是一切事物的根……真实的生活本身,要比画画与做雕刻更有价值,养孩子比画画或做生意更有价值。”
“我觉得我的作品藏在人民的心里,我一定要深深地抓住生活。”
凡高一生始终没有脱离“真实的生活”,他自己就是生活在最底层的人,在绘画上基本属于自学,这使他的作品脱离了学院派中规中矩的僵化与“正确”,他远远地走在了前面。他走得那么远,那么心无旁骛,以致于他既不能被那些平庸的同行认同与理解,也无法让那些傲慢的、唯利是图的画商看中。他的一生只卖出了一幅画,饥寒交迫,贫病交加,却始终不肯屈服。在安特卫普的美术学院,他看到了学院派那些毫无生命的作品,于是在信中告诉提奥:
“我在这里所见到的素描,在我看来都是很糟糕的,完全不行的。时间将会证明谁是谁非,学院派的老爷们或许会控诉我们是异端。”
时间的确早已证明谁是谁非,受尽冷遇与嘲讽的凡高,用作品告诉我们什么是真正的艺术,什么是真正的艺术家:
“它的周围有空气感,有颤动的光落在它的上面。”
这是凡高拿自己的人物画在与美术学院学生的作品进行比较时的发现。今天,当我们再来欣赏凡高的作品,那田野中的磨坊,夜间的咖啡馆,吃土豆的人,着红色圆点长裙的少女,我们可以真切地感受到那流动在画面中的空气和落在上面的颤动的光。
真正的艺术是不会被湮灭的。凡高死后,他作品的价值已经不能以金钱计。对此,凡高自己有过保守的预言:
“人们有一天总会了解,我的画的价值,要比我所花在画上的颜料价钱,以及我的生活(毕竟是十分贫寒的)费用高得多。”
今天,人们的确已经了解到这一点,但了解一个灵魂的价值远比了解一幅画的价值要困难得多。
我在这些书信的字里行间感受到了这个灵魂的存在,我甚至听到了急迫的呼吸,纵情的呐喊,触到了从田野上吹来的风,看到了在狂乱的风中决绝的奔跑……
“如果人们感到需要感受某种宏大的、无限的、使人感知到上帝的东西,那么他不需要到远处去找它。我以为我在婴儿的眼睛里,看到了比海洋还要深、还要无限、还要不朽的某种东西。”
凡高“在婴儿的眼睛里,看到了比海洋还要深、还要无限、还要不朽的某种东西”,我们在凡高的风景画和人物画里也看到了这种东西。在凡高为加勒医生画的肖像中,这位穿着蓝色外套的精神病医生靠在红色的桌子旁边,一手扶着桌面,一手托腮,紫色的水仙花,黄色的书籍,面孔瘦削,眼神宁静而和善,望着面前正在给他画像的凡高,望着每一位看他肖像的人。我盯着这幅肖像。我想摸一摸他头上那顶白色的帽子,从它凹塌下来的样子我能感受到质地的柔软。我想给他我的手,让他那宽大的有着凸出骨节的手握住,一定是粗糙的,有着舒适的温热。
这个懂得艺术与医术的好人,用极大的耐心与爱心,陪伴凡高走完了人生最后的岁月。我注意到加勒医生的这幅肖像作于1890年6月,正是凡高死前的一个月。
1890年2月,在发病的间歇,凡高完成了《开花的杏树》。背景是蓝绿色的天空,淡紫的殷殷的色块令人想到阳光的明媚,怒放的或是含苞的杏花开满枝头,枝条扭曲而虬劲,希望,潜力,坚忍,傲然,妩媚,奔放……空气中流动着杏花的芬芳,蜜蜂的嗡鸣像丝弦上奏出来的音乐。
这难道不是凡高一直追求的那种“比海洋还要深、还要无限、还要不朽的某种东西”么?
但那些保守而平庸的所谓艺术家与画商并没有停止对凡高的攻击与侮辱。毛威、戴尔斯蒂格等人相继离开了凡高,挖苦、讽刺他,并试图说服提奥断绝对凡高在经济上的援助。
“我时常陷入极大的痛苦,这是实在的,但是我的内心仍然是安静的,是纯粹的和谐的音乐,在最寒伧的小屋里,在最肮脏的角落里,我发现了图画。我的心怀着不可抗拒的力量靠拢这些事物。”
他靠拢着,热切地注视着、拥抱着世间美的一切。
“我认为一个农民姑娘的美,在于她满是灰尘与打了补丁的蓝色裙子与紧身胸衣;由于气候、风与太阳的影响,使她的服装具有最优美的色彩。如果她穿了一身贵妇人的服装,她就会失掉她那独特的魅力。”
这是凡高眼中的农民姑娘。
“一个穿黑衣服的、把她的一双小手搁在身后的小个子女人,静悄悄地沿着灰色的墙走来……一头黑发,一个小小的鹅蛋脸——棕色的或者是桔黄色的,我不知道。她有一忽儿抬起睫毛,用那对乌黑的眼睛斜扫过来。她是一个中国姑娘,神秘,安详,性格温柔。”
这是凡高眼中的中国姑娘。
这位“神秘,安详,性格温柔”的中国姑娘,走在1885年的安特卫普的街道上。衣衫褴褛的凡高看到了她的黑发,她的小小的鹅蛋脸和乌黑的眼睛。
“她有一忽儿抬起睫毛,用那对乌黑的眼睛斜扫过来。”或者,她也看到了凡高?
在无数孤独而颠沛流离的日子里,凡高常常在早上四点钟,就坐在阁楼的窗子前面,用透视工具画牧场与院子。他看见工人懒洋洋地走进院子,在屋顶的红瓦上面,一群白鸽在黑色的烟囱中间飞翔,这一切的后边,是广阔伸展开来的一片柔和、嫩绿,上面是一抹灰色的天空。于是——
“这种清早的景色,这些生活与睡醒的最初的标记,飞鸟,冒烟的烟囱、远在院子那边懒洋洋地行走的人——这些形成了我水彩画的题材。”
于是,大量美丽的作品诞生了。在他的同行们忙于卖画、展览的时候,在他的探索与尝试遭到无情地嘲讽与冷落的时候,他却可以傲然地向整个世界宣布——
“我时常尽情发笑,这是由于人们以各种各样的、恶毒与荒唐的事情来怀疑我,在这些事情中,我的头发没有一根是有罪的——我不是别的什么,而只是一个自然的朋友,研究的朋友,工作的朋友,尤其是普通人的朋友。”
“我的头发没有一根是有罪的”,这样的自信缘于他把表现自然,表现普通人,看成是一个画家的责任。
“一个艺术家不需要是一个牧师或者一个教堂的守门人,但是他一定要对他的同胞有一颗温暖的心。把一种理想放进自己的作品中,我认为这是一个画家的责任,我以为这是很高贵的……”
谁又能理解这种高贵呢?怀着一颗温暖的心,把一种理想融进作品中的画家在哪里呢?在很多时候,他孤独地走过街道,走进田野,在阴沉的雨季里,在寒冷的冬夜中,画着他眼中的世界。唯有绘画让他感到宁静。
“我要一再说明,每一个以爱与智慧从事创作的人,在他热爱自然与艺术的真心诚意中,会发现一种抵挡别人攻击的防护工具。自然是严峻的,也就是说冷酷的,但是它永远不会欺骗我们,并且始终帮助我们前进。所有这些东西使我感到心情开朗,精神振奋。”
一切伟大的灵魂注定是孤独的灵魂,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拥有爱与智慧。只有在孤独中,他才能听见真理发出的声音,才能看清楚“事物的本性”,才能以爱与智慧从事创作。而所有本真的东西,都将无所畏惧,因为没有人能遮蔽永恒。
“我通过人物与风景,想要表达的不是伤感,而是庄严的悲哀。简单地说,我要做到使人们看了我的作品后说:他是深深地感受的,他是亲切地感受的——尽管它粗糙,或许正是由于这一点,才表现了我的感受。”
但谁又能理解这“庄严的悲哀”?即使是“伤感”,也从来不曾有很多人领受过。一切喧嚣和活跃的背后,是无边无际的空虚和令人绝望的死寂。
“整个艺术事业腐朽了——我怀疑那些大价钱,即使是杰作的大价钱,是不是会维持下去。艺术品的价钱被提得那样高的时代,可以说,是在将来。”
历史竟不折不扣地成就了凡高的预言。今天,凡高的作品成为公认的杰作,但这些“公认”里面,依然让人怀疑有多少“真”的成分。毕竟,这是一个既“媚俗”又“媚雅”的时代。无论是“媚俗”还是“媚雅”,一样的虚伪,一样的令人生厌。
“人们不可能指望从生活中得到他已经明知道不能得到的东西,而且人们开始愈来愈明白地看到,生命只不过是一种播种的季节,收获不在此地。或许这便是人们有时候对社会上的意见漠然、无动于衷的原因。”
凡高一生都在播种,我们收获在此地,更多的人收获在未来。历史应该羞于回忆,虽然必须回忆。
“我在早晨一个人穿过城市,做了一次长途的步行,到了公园里,沿着林荫道走着。在空气中有一种使万物苏醒过来的清新东西,可是在事业上,在人与人之间,却多么令人灰心丧气啊!”
这种“使万物苏醒过来的清新东西”,包括爱情。
1881年,凡高遇到了西恩(凡高称她为“西恩”,意即别人的女人),她原名叫克丽丝蒂娜,是一个妓女,在怀孕后被抛弃,流落街头。走投无路之际,凡高收留了她,爱上了她。
戴尔斯蒂格嘲笑凡高:“这不恰像赶着一人驾驭的四马马车通过城市一样使人发笑吗?”
凡高有力地回击了这种傲慢的指摘与偏见:
“得啦,先生们,你们是一些自视为有漂亮风度与良好教养的人,你们认为抛弃一个女人,或者援助一个被遗弃的女人,哪一种更加优雅,更加高贵,更加有大丈夫气概?我所做的事,是十分单纯的与自然的,我以为我可以保留我的看法。我认为每一个有价值的人,在同样的情况下,也会这样做的。”
一个对人类怀着无尽的悲悯与同情的艺术家,当他单纯而自然的高贵无情地摧毁了那些正人君子们看似高雅的面具,他的孤独与寂寞就成了注定的命运。
所有美好的东西对凡高都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他追寻着真挚的爱情,在遇到西恩之前,他曾经深深地爱上了表姐,却遭到了无情的冷遇和永久的拒绝。他这样描述遭到拒绝时的心情:
“当这件事在今年夏天发生的时候,最初对我的打击,可怕得好像判处死刑,它一下子把我的心碎成齑粉。在这无法形容的精神的痛苦中,好像黑夜中的一线亮光一样,我的脑子里产生了一种思想:谁要是自愿退却的话,就让他这样办吧,但是谁要是有信心,就让他怀着信心吧!我打起精神来,不是退却,而是满怀信心。”
凡高的不退却和满怀的信心并没有挽回表姐的心。当他遇到西恩的时候,西恩的遭遇再一次唤起了艺术家深挚的爱情。
“我不止一次地不能抵抗爱情,常常是对那些被牧师在教坛上加以指摘的,认为是有罪的与被卑视的女人充满着爱。”
这个被卑视的女人,遇到了凡高,于是她悲苦的命运与一个伟大的灵魂有了最密切的关联。这样的补偿太多,尽管她不以为意。上帝对她实在过于眷顾,为了让她遇到凡高,所以让她流落街头。
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凡高尽力照顾着西恩,还收留了西恩年老的母亲,送西恩到医院分娩不属于他的孩子。他理直气壮地质问那些对他的行为表示不解的人:
“恋爱,求爱,生活之中不能没有爱情,这是罪恶吗?我以为没有爱情的生活才是一种罪恶,才是不道德的。”
没有爱情的生活竟是一种罪恶。人们追寻属于自己的爱情,就是使自己摆脱这种罪恶,把自己从不道德的深渊中解脱出来。我们还有理由拒绝爱情吗?
“一个人在恋爱之前与恋爱之后的区别,正好像一盏还没有点着的灯与一盏点着的灯之间的区别一样。现在灯已经摆在那里,而且是一盏好灯,而且也发光了。这是它真正的功能。爱情使人们对待许多事情采取更加沉着的态度,所以人们对自己的工作就更加满意了。”
追求爱情,就是要在心里点亮一盏灯,使自己不致于在黑暗中迷失。当这盏灯在我们的心里亮起来,我们就摆脱了恐惧,闪烁的火焰在欢快地跳跃,生命也在舞蹈。
西恩成了凡高的模特,她心甘情愿地给他摆出各种姿势。在凡高的笔下,曾经疾病缠身、形容枯槁的西恩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女人在她爱上别人与被别人爱着的时候,是会变样的;当没有人去关心她的时候,她精神颓丧,风姿消失。爱情把她内心所含有的东西引了出来,她的发展无疑是依靠这一点的。”
爱情点燃了生命的火焰,美就这样从内心深处被召唤出来。爱美的人类,不能没有爱情。
我长久地注视着凡高的一幅自画像。这幅肖像作于1889年9月。在圣雷米的精神病院里,不时发作的疾病已经严重摧垮了艺术家的身体,画中的凡高瘦削而苍白,胡须浓重,头发全部梳在脑后,紧锁的眉头,深陷的眼睛,眼神执拗而坚定地斜视过来。在这样的眼神里,那些不能被压抑的呼喊,那始终在奔涌的热情,那不肯屈服的灵魂,从松皱的衣服下,几乎要喷薄而出!
在阿尔的精神病院里,他甚至曾经这样设想:
“我怀着一种希望,凭着我对艺术的精通,即使在疯人院里,重新进行创作的时候一定会到来的。一个巴黎艺术家的矫揉造作的生活对我有什么用呢?我永远不会上它的当,我没有了最初具有的急于动身的热情。”
但是,他已经耗尽了最后的力气,可不屈的灵魂却依然执拗地燃烧。
“在许多人已经睡着,不愿意醒来,而有人却努力坚持一个人单独干的情况下,一个人单独干是有义务与责任的,因此那些睡着的人可以继续睡——或许这是比较好的情况吧!”
有人一辈子都在单独干,有人便可以趁此继续睡。愈来愈剧烈的发病使他决意进行最后一次抗争。这一次,他还是单独干。
1890年7月27日,凡高给提奥写了最后一封信。他来到田野,靠在一根树干上,子弹射进了胸膛,留给了弟弟提奥最后一句话:苦难永不会终结。
那些不愿醒来的人,可曾听见这愤怒的枪声?
在他的身下,是他曾经无数次沉醉在其中的广阔的麦田。
“我现在完全被衬着群山的广大无边的麦田吸引住了。平原辽阔如海洋,美妙的黄色,美妙的、温柔的绿色,一小片犁过与播下种子的土地的美妙的紫色——这片土地被开了花的土豆画上了绿色的格子;在这一切的上面,是带着美妙的蓝色、白色、粉红色、紫色调子的天空。”
所有的色彩都是美妙的。世界依然是美妙的。
毕竟——
“……在事物的本性上有使人精神振奋的东西,他们不会冻结、硬化,不会被顽固的偏见所阉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