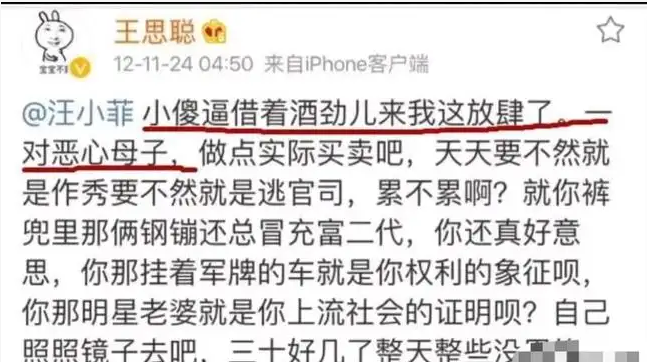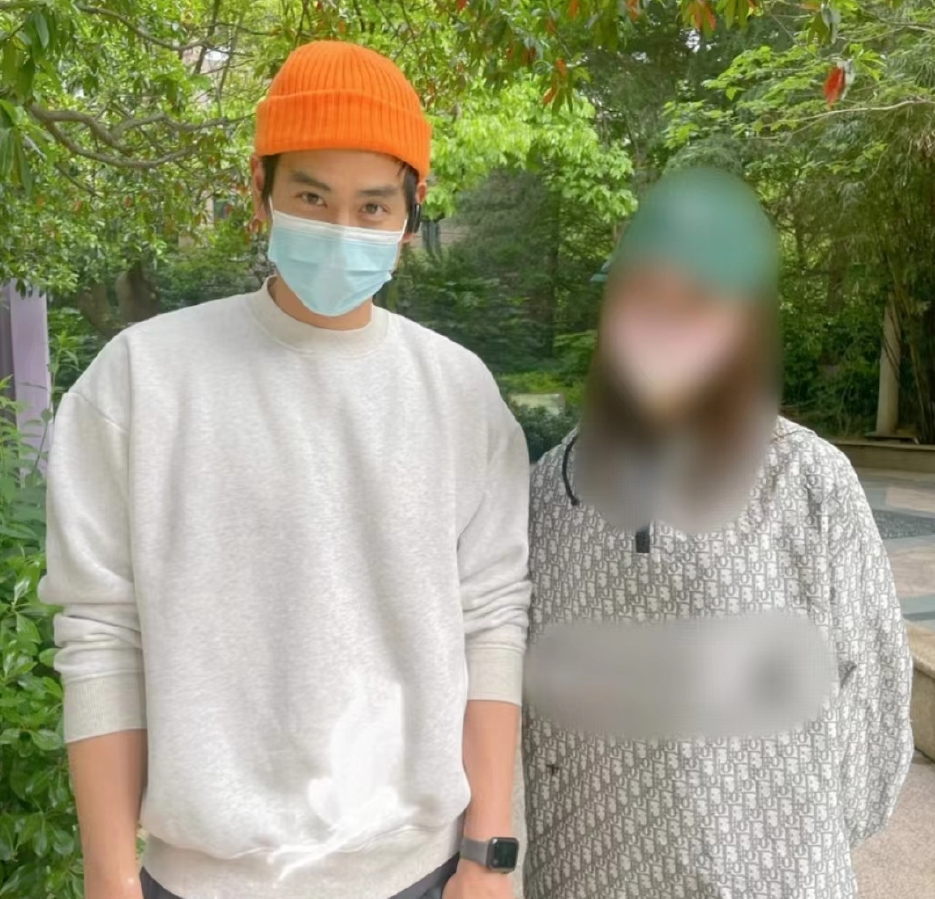□红孩
最近,好几个朋友要出版散文集,他们都希望我为其写个序言。写序言容易,无非介绍一下作者的情况、写作特点,或者围绕当前散文写作态势议论一番。但这样的序言我有些厌倦,主要原因是:一、大多数写作者散文题材、手法比较类型化,常常让我无话可说。二、我这二十年关于散文理论已经写了一百多篇,并且结集出版为《红孩散文说》,关于散文的话题似乎说尽了。
我相信,对于我目前所处的尴尬,很多散文名家或散文理论家都会有同感。二十几年前,贾平凹曾提出大散文的概念,后来有一批年轻的散文家又提出新散文,甚至有人提出散文革命,我为此写出了几篇支持或不支持的文章,譬如:《见怪不怪的散文八怪》《散文向哪里革命》《关于散文的哲学思考》等,对散文的大与小、新与旧、创新还是坚守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得到很多同行的赞许,当然也有不同的争论。回过头看,自己也好,别人也罢,不论怎样谈,散文的诸多问题始终没有得到确定的肯定。
这不奇怪。关于散文的争论,还是出在散文本身。作为文学的文体之一,散文的概念本来就是模糊的。如果从古代沿用的韵文之外皆散文,即诗歌之外皆散文,那问题就好解决了。可是,自白话文学以来,散文和小说、报告文学、诗歌、寓言、童话、戏剧,甚至散文内部的评论、随笔、杂文、小品文,即使是同一母体的散文诗也都彻底分裂开来。那么,散文究竟是什么样的呢?这让很多人陷入了困惑。这不禁让人想到盲人摸象,欧阳修、王安石等人摸了,鲁迅、朱自清、冰心、沈从文、巴金摸了,杨朔、秦牧、刘白羽、孙犁、汪曾祺、贾平凹、铁凝、迟子建等也都摸了,虽然他们摸得都很精彩,可没有一个人能概括大象的全部。我相信,即使再过500年,也不会有人能说出大象,也就是散文的根本特征。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后,特别是到了九十年代,很多散文写作者越来越不愿看那些所谓的歌德式杨朔体散文写作。在这前十年间,诗歌、小说、报告文学则经历了揭露、反思、伤痕、寻根的突变,散文则近乎按兵不动。人们对散文的认识更多还停留在朱自清、冰心、杨朔模式。直到巴金《随想录》的出现,人们才恍然大悟,散文居然可以这样写。等到余秋雨文化思考型散文和季羡林、张中行等学者型散文的出现,才真正把散文的天空给大大拓宽了。但紧跟的问题又出现了,一个作家或一群作家的风格出现了,就会出现步后尘的无数模仿者。这就有意思了,过去反对别人想革别人命的人,如今又成了被他人革命的对象。我觉得这很正常,艺术所以成为艺术,就是不断被否定颠覆的过程。
这十几年,我听不少散文写家总叨唠现在的散文太像散文了。大概是对散文类型化的不满吧。作为长期从事散文写作、编辑的人,我也深有同感,可我又不免心有疑存,散文如果不像散文还能像什么?总不至于像小说像新闻像总结报告像大会演讲吧。不管散文怎样发展,文学性总要讲吧,叙事抒情不可回避吧,文化思考哲学审美总要追求吧?我不大同意把散文的界定无限放宽,什么都往散文的筐里装。反之,我也不大同意把散文的界定规定得过窄,那样,散文会限制散文自身的发展,甚至让散文无路可走。既然如此,那只好选择中间道路,那谁又来规定这道路的规则呢?到底是四车道五车道,还是八车道九车道?我以为,任何人任何机构都没有这个权威。
前几天,一个朋友给我发来燕子南飞的图片。过去,一说北燕南飞,人们总以为那燕子肯定要飞到长江以南。可是,根据科学家发现,那些北燕根本没有飞到江南,而是经河北、内蒙古、新疆飞到中亚,最后到达非洲,全程2.5万公里,历时三个月。这一惊人的发现,着实吓我一跳!我觉得,写散文比北燕南飞还难以琢磨,只要人类靠文字表达,它就没有终极的目标。当然,散文也会像燕子一样,它飞行的方向不一定永远南飞,随着季节的变化,它也会往北飞,这就叫适者生存。说得直白些,散文的变是永恒的,不变终究是要被淘汰的。但不管怎样变,散文的模样总还是要有的,如果硬要我画出散文的样子,我只能说,您尽管看我的散文好了。我想,这句话对于其他作家也同样适用。